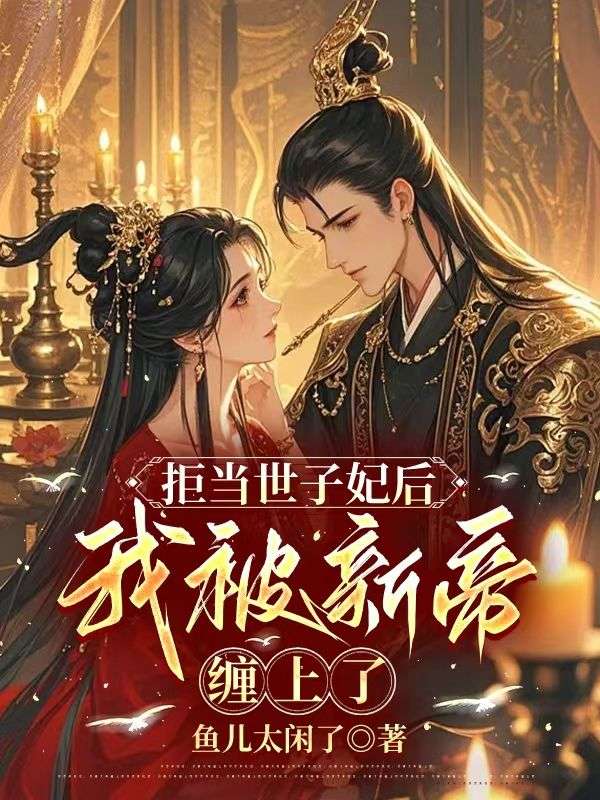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
第4章
宋朝陽已來到了徐家。
徐少陵的家當真可用家徒四壁來形容,房中除了兩張木榻和一個老舊的櫃子,再無長物。
初春季節,冰雪還沒化透,屋裏半點火星都沒有,比外邊暖不了多少。
此情此景,宋朝陽忽然想起了夢中的一句話,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,必先苦其筋骨,勞其體膚!
“娘,這位就是孩兒與您說的女貴人,聽說娘摔了,還特地找來了大夫。”
徐少陵動作輕柔的扶起母親,宋朝陽已經看到了徐母腫脹的右腿。
“多謝女貴人,少陵給您添麻煩了。”
徐母欲起身道謝,被宋朝陽攔住。
“伯母不必多禮,看病要緊,大夫,麻煩了。”
宋朝陽聲音柔和,舉止端莊,頓讓徐母局促的心放鬆了不少。
一盞茶後,大夫道:“隻是扭了筋,算是不幸中的大幸,吃些補養之物,再好生休息半個月,便可恢複了。”
徐少陵趕緊上前道謝,大夫給開了兩記方子,徐少陵送大夫離開,順便抓藥,宋朝陽亦起身和徐母辭行。
“工匠可都找好了?”
出了院門,宋朝陽問了一句。
“找好了,隻是不知要如何修整,正在等小姐吩咐。”
徐少陵有些愧疚。
“因為我娘,耽誤了小姐的正事,實在是對不住。”
“無妨。”
宋朝陽從袖子中拿出了一張紙,遞給了徐少陵。
“這是我畫的圖樣,可按這個修整,你不必擔心銀子,多少些能人巧將,時間越快越好,再張貼些榜文,招幾個夥計廚子,以及靠譜的掌櫃。”
“是。”
徐少陵小心翼翼的接下來圖紙,又有些不解。
都找全了,他豈不是又要重新尋找生計了?
他猶豫了一下,躬身說道:“少陵願領小二一職,還望小姐成全。”
宋朝陽抿嘴一笑道:“你可做幕後老板,幫我管理這個酒樓,所賺的銀錢你我三七分成,其餘時間......你還是去讀書吧。”
徐少陵徹底的愣住了。
天下間當真會有如此好事?
他究竟是在做夢,還是得了耳疾!
宋朝陽將另外一份紙契遞給了他。
“空口無憑,立字為證,隻是酒樓的運做也需要點時間,在沒有盈利之前,每個月我給你十兩銀子做薪俸。”
父親和外公都是朝中官員,宋朝陽又是一個女眷,自然不便拋頭露麵,到不如效仿秦清,自己當個甩手掌櫃。
而且,彼時她這種做法對徐少陵來說,無異於雪中送炭。
想到這,她又說道:“南橋下有個寫對子的李先生,他當掌櫃就很合適,你去找他,他定然應允。”
徐少陵心情複雜的看著紙上的字,自打記事,他遭受了無盡的謾罵與冷眼,還是第一次有人能如此信他,看重他。
一撩長袍,便欲跪下,宋朝陽嚇了一跳,他的跪,她可擔不起,會折壽的。
她扶住了徐少陵的手臂,意識到男女授受不親,又迅速的收了回來。
“徐公子不必多禮,權當是緣分使然,你若想尋我,就去去戶部尚書的府中找二小姐宋清月,她自會幫你轉達,但是,這件事千萬不要告與別人。”
宋朝陽囑咐了一句,便道:“快去買藥吧。”
在外邊站了一會,她已冷的發抖,趕緊上了馬車。
徐少陵目送馬車離開,心頭一陣溫熱。
無論付出多少心血,他都要幫女貴人料理好酒樓,以報她知遇之恩。
“少陵!”
清脆的呼喊讓徐少陵回過神兒。
“秦清,你怎麼回來了?”
秦清跑的臉色發紅,微微喘息。
“聽小五子說徐大娘摔傷了腿,我便回來了,這是這兩日賣的茶錢,你快拿去給徐大娘治病。”
秦清把幾個銅錢塞給了徐少陵,卻被徐少陵推了回去。
“伯父的身體也不好,你留著給大伯買些補品,我這有些銀子,夠抓藥的。”
“酒樓的老板給你結算工錢了?”
秦清詫異的問。
“不是,酒樓昨日就賣掉了,這些銀子是買鋪子的貴人借我的,你放心,日後我定然會還的。”
徐少陵能感覺到宋朝陽必然大有來頭,否則不能讓他做幕後的老板,人家對自己有恩,萬不能將她暴露。
聽了徐少陵的話,秦清露出了惋惜的神情。
她一早就看中了那個酒樓,不想竟被別人先得了手。
徐少陵知道她的心思,安慰道:“西街位置偏僻,等我賺了錢,定會幫你買個更好的。”
秦清頓時甜甜的笑了。
“謝謝少陵!”
王府。
春日,天黑的早,宋朝陽回到王府,門外已經亮起了風燈。
她緊了緊身上的披風,快步進門。
沒走兩步,就被盧雪顏給攔住了。
“一整天都不見個人,你跑哪去了,已經嫁做人婦,卻整日往外邊跑,成何體統,王府的臉都被你給丟盡了。”
宋朝陽聲音淡淡。
“我去哪裏,用得著和盧小姐報備嗎,盧小姐好歹也出生於禮儀之家,如此反客為主,不覺太過了嗎?我勸你還是安分一些。”
盧雪顏微微一怔,自從宋朝陽落水,她已有半個月未見過她了,平日裏,宋朝陽慣會討好自己,如今居然敢用這種態度對她說話,莫不是腦袋裏進水了?
“呸,王爺和王妃都沒趕我走,你居然敢跟我說這種話,找打!”
盧雪顏揚起了手,宋朝陽站在原地沒有動,凍得發白的嘴角微微揚起,譏諷的看著盧雪顏。
“敢動手嗎,我勸你還是掂量掂量自己的身份,再好好想清楚,王府當家的是誰。”
想到自己凋零的家門,盧雪顏硬生生收回了手,如今她已沒了可以依靠的母家,能指望的隻有姨母了。
想到此處,她又換了一種說辭。
“王府不比尋常百姓家,你整日濃妝豔抹,跑到破落的館子裏和那些粗鄙的男人一起喝茶,莫不是耐不住寂寞,想偷人了?”
啪,一耳光抽在了盧雪顏的臉上。
宋朝陽冷聲叱道:“放肆,我不過是覺得秦姑娘泡的茶好喝,到了你嘴裏竟變得如此不堪,若非你心有齷齪,便不會說出這種下作的話來。”